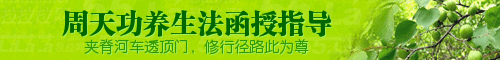(二)制心止。制心者,随其心念起处,制之使不流动也。习系缘止后,稍稍纯熟,即当修制心止。是由粗入细之法。
盖所谓心者,若细言之,则有心王、心所种种之名词。然若就现在专谈用功之便利而简单言之,即将心字看作胡思乱想之心亦可也。今所言制心止者,制之之法,即是随吾人心念起处。断其攀缘以制止之。心若能静,则不须制,是即修制心止。
然有意制心,心既是一个妄念,制又是一个妄念,以妄制妄,其妄益增。譬如家有盗贼进门,主人起而与之抵抗,未必能胜,反或被害。倘端坐室中,目注盗贼,毫不为动,则盗贼莫测所以,势必逡巡退出。故余常用一种简便方法,于入坐时,先将身心一切放下,然后回光返照,于前念已灭,后念未起之间,看清念头所起之处,一直照下,不令自甲缘乙。于是此妄念自然销落,而达于无念之境。念头再起,即再用此法。余久习之,极有效验,此犹目注盗贼,令其逡巡自退也。
(三)体真止。此法更较制心止为细。前二法为修止之方便,此法乃真正之修止。又,制心止可破系缘止,体真止可破制心止,是由浅入深,由粗入细之工夫。
体是体会,真是真实。细细体会心中所念一切事事物物皆是虚妄,了无实在,则心不取。若心不取,则无依无著。妄想颠倒,毋须有意制之,自然止息。是名体真止。
至于修体真止之法,当于坐时先返观余身自幼而壮、而老、而死,刻刻变迁,刹那刹那不得停住。倘吾身有一毫实在者当有停住,今实无法可使之住,可知吾身全是因缘假合假散。又返观余心,念念迁流。过去之念已谢,现在之念不停,未来之念未至,究竟可执著哪一念为我之心耶?如是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际周遍求之,了不可得。既不可得,则无复有心。无心则无生,又何有灭?吾人自觉有妄心生灭者,皆是虚妄颠倒,有此迷惑。久久纯熟,其心得住,自然能止,止无所止,方为体真止也。
此所言者,乃专言用功之方法耳。若据实而论,则吾人此身,乃是烦恼业识为因,父母为缘,因缘凑合而成者也。又唯心之外,别无境界。所谓一切唯心是也。
第二节 修 观
观是观察,内而身心,外而山河大地,皆当—一观察之。而以回光返照,为修持之主旨。今因对治三毒,为说三种观法。对治者,吾人应自己觉察贪瞋痴三毒,何者偏多,即对此病而修观法以治之也。
(-)淫欲多者,应修不净观。试思吾身受胎,无非父母精血、污秽不净之物和合而成。胎之地位,在母腹肠脏粪秽之处。出胎以后,得此不净之身。从头至足,自外至内,不净之物,充满其中。外则两眼、两耳、两鼻孔及口、大小便,共计九窍,无时不流臭液。遍身毛孔,发散汗垢。内察脏腑,脓血尿屎、种种不净。及其死也,不久腐烂,奇臭难闻。如是男观女身,如一革囊。外形虽美,内实满贮粪臭。女观男身,亦应如是。久久观察,淫欲自减。是为对治淫欲修不净观。
(二)瞋恚多者,应修慈悲观。当念我与众生,本皆平等,有何彼此分别?慈者,推己及人,与以快乐也。若我身心,愿得种种快乐,如寒时得衣,饥时得食,劳倦时得休息之类。应发慈心,推广此等快乐,及于我之亲爱。修习既久,应推及疏远之人,更进而推及向所怨憎之人。怨亲平等,了无分别,方谓大慈。悲者,悲悯众生种种苦恼,我为拔除之也。亦对亲疏怨增了无分别,方谓大悲。如此常常观察,瞋恚之病自然消除。是为对治瞋恚修慈悲观。
(三)愚痴者,应修因缘观。愚痴即是无明,三毒之中,最难破除。故亦得谓前二法为修观之方便,此法是真正之修观。世间一切事物,皆从内因、外缘而生。如种子为因,水土时节为缘,因缘凑合,种能生芽,从芽生叶,从叶生节,从节生茎,从茎生华,从华生实。无种子,即不能生芽以至生实。无水土,种子亦不能生芽生实。时节未到,种子亦不能生芽以至生实。然种子决不念我能生芽,芽亦不念我从种子生,水土亦不言我能令种子生芽以至生实,时节亦不言我能令种子生芽以至生实。可见凡物之生,了无自性。若有自性,即应永久常住,不应因缘凑合而生,因缘分散而死。我身亦然,前生之业为因,父母为缘,因缘凑合即生,因缘分散即死。死死生生,生生死死,刹那刹那,不得稍住。如是常常观察,自能豁破愚痴,发生智慧。是为对治愚痴修因缘观。
以上止观二法,在文字上记述之便利,自不得—一罗列。至于实际修持,则愈简单愈妙。宜就各人性之所近,择一法修之,或多取几法试之。察其何法与我相宜,则抱定一法,恒久行之,不必改变。此应注意者也。
第三节 止 观 双 修
前文所述止观方法,虽似有区别,然不过修持时,一心之运用方向,或偏于止,或偏于观耳。实则念念归一为止,了了分明为观。止时决不能离观,观时决不能离止。止若无观,心必昏沉。观若无止,心必散乱。故必二者双修,方得有效。今略举如下。
一、对治浮沉之心,双修止观。静坐时,若心浮动,轻躁不安,应修止以止之。若心昏暗,时欲沉睡,应修观以照之。观照以后,心尚不觉清明,又应用止止之。总之当随各人所宜,以期适用。若用止时,自觉身心安静,可知宜于用止,即用止以安心。若于观中,自觉心神明净,可知宜于用观,即用观以安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