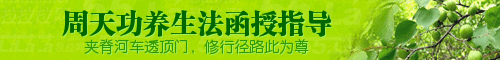方今末世,众生根器浅薄,修小乘得果者亦绝不一见矣,况修大乘者乎?故有志修行者,多用禅净双修之法。
止观即禅门之一法,此法全凭自力了澈本性,如泅水者逆流而上,直穷生死大海。初非易易,故即身证果者少。
净,即净土。此法则依仗阿弥陀佛之力,如得渡船横渡生死流,自易达于彼岸。然须信、愿、行三者不可缺一,方得有效。
信者,深信净土,毫无疑虑。愿者,发愿我于临命终时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。行者,念佛功夫力行不怠,功夫积久,自然于命终之时一心不乱,可以见佛往生。
此则余所目见耳闻者事实甚多,决非虚语,故余主张禅净双修,自、他之力兼用也。读者其有意乎?
我佛世尊以一大事因缘,出现于世。所谓大事因缘者何?即吾人之生死问题是也。试想人生于世,虽寿有修短,总不过数十寒暑。庸碌者虚度一生,即杰出者能作一番事业,尽世间之责任,然若问吾人究竟归宿应如何?人生最后之大目的应何在?鲜有不猛然警醒,而未易置答者。孔子云:“未知生,焉知死?”盖孔子但言世间法,故对此问题,存而不论。佛则于世间法外,特重出世间法。目睹众生生死轮回之若,以身作则,舍王太子位,而入雪山修苦行六年,遂成正觉。说法四十九年,慈悲度众。无非教人超出生死大海,免堕轮回。此佛教之所由来也。
欲勘破生死关头,当先知吾人所以流转生死之根本。此根本惟何?在佛家称之曰“阿黎耶识”。照心理学上之三分法,分人心之作用为知、情、意。于意识之外,未能再加推勘,有所深入。无他,凡夫知识之界限,只到此为止也。佛家则返观自心,于意识之外,尚窥见几种心识。乃分人心为八识,以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为前五识,以意为第六识,此外有第七识,译名“末那”,犹言执我也。第八识译名“阿黎耶”,犹言含藏也。推勘至此,始知吾人生死之根本,即在阿黎耶识。
阿黎耶识何以能为生死根本?盖此识乃是真心与妄心和合之识也。此真心非指吾人肉团之心而言,乃吾人之净心是也。因其尚与妄心和合,故名之为阿黎耶识。此识中含有不生、不灭及生灭二义,所谓真妄和合者也。不生、不灭是觉。生、灭即是不觉。我辈凡夫只是妄心用事,念念相续,攀缘不已,无始以来就是不觉,故颠倒于生死海中,莫能自拔。然妄心真心本为一体,并非二物。真心譬如海水,妄心譬如波浪。海水本来平静,因风鼓动遂成波浪。此波浪即是海水鼓动所成,非另为一物,犹之妄心因真心妄动而成也。我辈凡夫病在迷真逐妄,佛家教人修行方法虽多,总是教人从对治妄念下手。一言蔽之,即背妄归真而已。
然则吾人妄心之生、灭形状若何?《大乘起信论》中,曾言其生起之相,细者有三,粗者有六。
何谓三细相?
一曰无明业相。盖言真心不动,则是光明。一经妄动,即生诸苦。犹如明境为黑暗所蔽,故名无明。
二曰能见相。真心不动时,无所谓见。一经妄动,便生妄见。是谓能见相。
三曰境界相。吾人躯壳及周围环境,以及大地山河,皆为境界。以有能见之妄见,遂呈此妄现之境界。实则一切无非幻象,惜吾人梦梦不能觉察耳。
此三种细相同时而现,极其细微,不易窥见,而皆由无明所起。所谓无明为因生三细也。
何谓六粗相?
一曰智相。既有境界妄现,我们即从而有认识。认识以后,即起分别。遇顺境则爱,遇逆境则不爱。皆所谓智也。
二曰相续相。因有爱与不爱之念,存于心中。爱则生乐,不爱则生苦。念念相续,无有穷时。
以上二相,虽有顺逆苦乐,尚未至作善恶地步也。
三曰执取相。既有苦乐,即有执著。或困于苦境而不能脱离,或耽于乐境而不肯放舍,皆执取也。
四曰计名字相。因有执取之境,心中必安立名言,计度分别。前者执取,尚似实际苦乐之境。至于计名字,则并无实境,惟是心中计度。而作善作恶,乃将见于行为矣。
五曰起业相。因计度名字必寻名取得实境,遂不免造出种种善恶之业。
六曰业系苦相。既造业必受报,善业善报,恶业恶报,要皆足以束缚吾人,使不得自在。不自在,即苦也。试思在世为人,孰有不为业所系者乎?
此六粗相皆由境界而起,所谓境界为缘,长六粗相也。
吾人无论为善、为恶,皆是为业所系,此犹疾病之在身也。佛为医王,佛法即医药。药方虽种种不同,而其能治病则—。治病下手之始,最要就是对治妄念。治妄念首在破执。执有二:
一曰我执。吾人自母胎降生后。别种智识,全未发达,而我字之一念必先来。如生而即知求食,以维持吾之生命是也。下等动物,如遇宰割,亦知叫唤,即恐丧失其生命也。须知我执为一切罪恶之源,盖有我则不知有人。人我分别之见愈深,必见于行为而成罪恶也。然刻实论之,我之实在,乃了不可得,善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