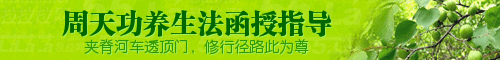二、对治定中细心,双修止观。止观法门,习之既久,粗乱之心渐息,即得入定。定中心细,自觉此身,如同太虚,十分快乐。若不知此快乐本来虚妄,而生贪著,执为实有,则必发生障碍,不得解脱。若知是虚妄不实,不贪不执,是为修止。虽修止后,犹有一毫执著之念,应当观此定中细心与粗乱之妄心,不过有粗细之别,毕竟同是虚妄不实。一经照了,即不执著定见。不执定见,则功候纯熟,自得解脱。是名修观。
三、均齐定慧,双修止观。修止功久,妄念销落,能得禅定。修观功久,豁然开悟,能生真慧。定多慧少,则为痴定。尔时应当修观照,使心境了了明明。慧多定少,则发狂慧。心即动散,如风中之灯,照物不能明了。尔时应复修止,则得定心,如密室中之灯,照物历历分明。是谓止观双修,定慧均等。
第四节 随时对境修止观
自第二章第一节至第三节,所述止观方法,皆于静坐中修之。密室端坐,固为入道之要。然此身决不能无俗事牵累,若于静坐之外,不复修持,则功夫间断,非所宜也。故必于一切时,一切境常常修之方可。
何谓一切时?曰行时,曰住时,曰坐时,曰卧时,曰作事时,曰言语时。
云何行时修止观?
吾入于行时,应作是念:我今为何事欲行?若为烦恼及不善事无益事,即不应行。若为善事有益事,即应行。若于行时,了知因有行故,则有一切烦恼、善恶等业,了知行心,及行中所现动作,皆是虚妄不实。毫不可得,则妄念自息。是名行中修止。又应作是念:由先起心以动其身,见于行为,因有此行,则有一切烦恼,善恶等业。即当返观行心。念念迁流,了无实在,可知行者及行中所现动作,毕竟空寂。是名行中修观。
云何住时修止观?
吾人于住时,应作是念:我今为何事欲住?若为烦恼及不善事、无益事,即不应住。若为善事、有益事,即应住。若于住时,了知因有住故,则有一切烦恼、善恶等业。了知住心及住中所现状态皆是虚妄不实,毫不可得,则妄念自息。是名住中修止。又应作是念:由先起心以驻其身,见其住立,因有此住,则有一切烦恼,善恶等业。即当返观其心,念念迁流,了无实在,可知住者及住中所现状态,毕竟空寂。是名住中修观。
云何坐时修止观?
此坐非指静坐,乃指寻常散坐而言。吾人于坐时,应作是念:我今为何事欲坐?若为烦恼及不善事、无益事,即不应坐。若为善事、有益事,即应坐。若于坐时,了知因有坐故,则有一切烦恼、善恶等业。了知坐心及坐中所现状态,皆是虚妄不实,毫不可得,则妄念自息。是名坐中修止。又应作是念:由先起心以安其身,见此坐相,因有此坐,则有一切烦恼,善恶等业。即当返观坐心,念念迁流,了无实在,可知坐者及坐中所现状态,毕竟空寂。是名坐中修观。
云何卧时修止观?
吾人于卧时,应作是念:我今为何等事欲卧?若为不善、放逸等事,即不应卧。若为调和身心,即应卧。若于卧时,了知因有卧故,则有一切烦恼、善恶等幻梦,皆是虚妄不实,毫不可得,则妄念自然不起。是名卧中修止。又应作是念:由于劳乏,即便昏暗,见此卧相,因有一切烦恼,善恶等业。即当返观卧心,念念迁流,了无实在,可知卧者及卧中所现情状,毕竟空寂。是名卧中修观。
云何作事时修止观?
吾人于作事时,应作是念:我今为何等事欲如此作?若为不善事、无益事,即不应作。若为善事、有益事,即应作。若于作时,了知因有作故,则有一切善恶等业,皆是虚妄不实,毫不可得,则妄念不起。是名作中修止。又应作是念:由先起心,运其身手,方见造作,因此有一切善恶等业。即当返观作心,念念迁流,了无实在,可知作者及作中所经情景,毕竟空寂。是名作中修观。
云何言语时修止观?
吾人于言语时,应作是念:我今为何事欲语?若为烦恼及不善事、无益事,即不应语。若为善事、有益事,即应语。若于语时,了知因此语故,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业,皆是虚妄不实,毫不可得,则妄念自息。是名言语中修止。又应作是念:由心鼓动气息,冲于咽喉唇舌齿颚,故出音声语言,因此有一切烦恼善恶等业。即当返观语心,念念迁流,了无实在,可知语者及语中所有音响,毕竟空寂。是名语中修观。
何谓一切境?即六根所对之六尘境,眼对色,耳对声,鼻对香,舌对味,身对触,意对法也。